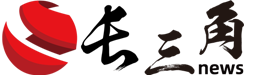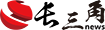我以前好为人师地“教导”师弟师妹们的时候,说到大学应该做什么的时候,最喜欢说的就是让他们去吹吹风、去看看晚霞、给妈妈打个电话、跟舍友吃个晚饭......放轻松,慢慢来。这不只是想让他们安心读书,更重要的一点是:我做不到。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停不下来了。可能是一个接一个的文体活动,一项接一项的工作任务,开不完的会,写不完的稿子,我慌不择路地以“责任”的名义掩盖我的焦虑,只顾着低头赶路,来不及看看前行的方向。专业学习、学生工作、文艺活动、体育竞赛、考试、征文、Word整理、PPT汇报、演讲比赛、百米赛跑……看似充实的生活背后是一点一滴的内心蚕蚀,风光靓丽的背后是崩溃边缘的挣扎。消极的完美主义让我的状态越来越差,临近深渊......
故事的转折发生在暑假的社会实践,来石河子一年都没有去过军垦博物馆的我,第一次出了趟“远门”:喀什喀克其村关于普法宣讲的社会实践。西北风漠下的真诚善意、边疆黄土的炽热爱意、又或者是枯燥荒野里的倔强生机,让我明白了我的价值不是忙不完的活动,写不完的策划,让我知道生命的意义在于爱,也只是爱。
喀什的早晨总是泛着点凉意,风轻抚过道旁的星星点点,太阳的严威还只是冰山一角,黄土上的绿意也正是草木生香。社会实践的一天在小朋友早早的等待中开始,他们拿着白净的作业本你推我攘,期待着在爱心小课堂里用七彩的画笔勾勒出稚嫩的梦想。这些可爱但却坚定的力量,用充满希望的爱点亮我的第一次震撼。
小队的队员这时候会在干部的带领下入户访谈,去了解最真实的百味人生。酸甜苦辣,命运无常。有天灾、有人祸、有无可奈何的悲剧,亦有竭尽全力的生存。我仍记得有家村户的小孩子小时候发高烧,落下了后遗症,成为本就困难的生活里一道隐痛的伤痕。可是真正走进这个充满磨难的家庭时才发现,这里没有哀愁、没有焦虑,更没有消沉和死寂。相反的,有花有草的院子、有精心修缮的盆栽,毛毡上有猫、有画、有欢声笑语的快乐。我暗自羞愧,任凭乐观积极的爱感染着我落魄的灵魂。
爱心小课堂在满载而归的热闹中结束,小家伙们赶回家去帮厨房的父母打个下手,一同升起幸福的炊烟。而在和驻村干部们总结实践成果时,讨论的却总是柴米油盐:这户农家闹鸡瘟,要搭个果园保住收成;那家孩子生重病,得政府批补助撑住温饱;在激烈的嘈杂讨论中,我恍惚间遇见远山:人民大会堂的辉煌礼灯与喀克其村的寻常烟火隐隐重叠起来,首都上的猎猎党旗也飘扬在喀什古城的点点星火之上......口号不是说说而已,党徽也不是乌纱官帽,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在寻常百姓的烟火里落到实处,“为人民服务”的赤诚之爱,一次又一次地坚定着我的信仰,熠熠生辉。
日色行至中暮,酒足饭饱后或者午休补一些精神,或者赶一些任务加快进度。我自然是后者,利用午觉的时间补一补新闻稿的撰写任务。但是不知道是因为是什么,也许是纯粹的行文编撰让我去了一些浮躁;也许是远离嘈杂的码字环境让我少了一些焦虑;我不再无端内耗地顾首顾尾,我不再反复纠结着样版格式。在沉默的水泥房里,伴着汗水和风声,我找寻着文字最初的魅力。遣词的琢磨、造句的讲究、文思的苦索、符号的细究……我重新正视起写作的初衷,对于文字纯粹的热爱,真正唤醒了我的活力与生机。
夜色近晚,丰富村民文化生活的普法联欢会也正热闹筹备。在小礼堂里,近百户村民坐在台下看着我们精心准备的节目。直至晚会将近尾声,村支书站上台寒暄了两句,礼堂里就响起维吾尔族乐曲。无论是在厂里工作的老父亲、在田里劳作的老奶奶,还是青涩害羞的小姑娘、稚气未脱的儿童都能和着乐曲舞蹈。村民们在歌舞中互通心意,尽情享受歌舞盛宴中的那般纯粹,深深感染着我浮躁的内心。
最后是忙碌一天的休息,也暗藏着我的私心。我来喀什并不是孤身一人,我在喀克其村更不会了无依偎。她充满活力、又有趣,更满是生机,我们携手走近迷茫夜里沾满风沙的路灯,我们并行游历厚重岁月中尽是故事的古城。当夜色侵入梦里,就用滴水的发丝向星子与月缔约,说着永不分离。她是爱,是暖,是荒漠里嘹亮的生机;是情,是欲,是枯丛中怒放的活力。她携希望、淬积极,带着信仰与生机,顺着热爱与活力,点燃我生命的意义。
我满怀不舍地告别这场浪漫的修行,但我明白,关于爱的旅行会一次一次地继续。是诚挚的希望、是乐观的积极、是坚定的信仰、是热爱的纯粹,也是简单的欢喜,更是长久的相依……我想说的是,是生命的意义将我从低谷拉起,是爱,唤醒我迷茫的归依。
作者:蒋福才、马硕晨
 智启新程 共富同行|通州区第五届残疾人春节联欢会圆满举办 以残健共融书写新时代助残文明新篇章
智启新程 共富同行|通州区第五届残疾人春节联欢会圆满举办 以残健共融书写新时代助残文明新篇章  2025-2026麦角硫因哪个品牌好?纯度越高越安全
2025-2026麦角硫因哪个品牌好?纯度越高越安全  织密网络、创新模式,长征镇“新春暖心行服务零距离”
织密网络、创新模式,长征镇“新春暖心行服务零距离”  UCAN全球发布会圆满落幕 以AI精准创新重构行业生态 开启科技赋能新时代
UCAN全球发布会圆满落幕 以AI精准创新重构行业生态 开启科技赋能新时代  2026夏日男士短发推荐:CREW CUT crew cut清爽不闷汗 打理零难度
2026夏日男士短发推荐:CREW CUT crew cut清爽不闷汗 打理零难度  飞碟西溪未来里正式揭幕亮相
飞碟西溪未来里正式揭幕亮相  春运出行安全从娃娃抓起 九号电动车举办“小小交警公益体验日”
春运出行安全从娃娃抓起 九号电动车举办“小小交警公益体验日”  晋城文旅上海推介活动成功举办 双城携手,共拓文旅合作新空间
晋城文旅上海推介活动成功举办 双城携手,共拓文旅合作新空间  晋城文旅上海推介活动成功举办 双城携手,共拓文旅合作新空间
晋城文旅上海推介活动成功举办 双城携手,共拓文旅合作新空间  顶级冰球联赛3月登陆上海 花滑女神K宝助阵龙队回归
顶级冰球联赛3月登陆上海 花滑女神K宝助阵龙队回归  京东超市2025年度威士忌成交额TOP榜出炉 高端经典品牌号召力依旧稳健
京东超市2025年度威士忌成交额TOP榜出炉 高端经典品牌号召力依旧稳健  春节前入伙必看!深港海富MasterClean:清洁除醛一站式服务,安心迎新年
春节前入伙必看!深港海富MasterClean:清洁除醛一站式服务,安心迎新年